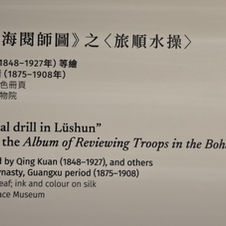修明武備 — 清代軍事文物
清朝(1644–1911 年)是滿族統治的政權,其武力基礎建立於嚴謹的軍事組織、卓越的軍事技術和獨特的尚武精神之上。紫禁城作為政治軍事的中樞,承載了清朝二百餘年的軍事記憶,充分反映滿族承繼尚武祖訓、汲取軍事技術並加以創新,以及創建禮制的文化取徑,是典藏傳統軍事文化的豐富寶庫。展覽展出約190 件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軍事文物,包括盔、弓箭、刀劍、馬具、繪畫、織品、圖籍和科學儀器等眾多類別的豐富文物。



龍興八旗
清太祖努爾哈赤以傳統狩獵組織為基礎建立的八旗制度,以及其後陸續設置的各種專業部隊。
八旗制度是清朝建立的多族群聯合社會軍事組織,由努爾哈赤於1615年創建,分為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共八個旗色,後期又增設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該制度在軍事、行政和生產方面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清朝的征戰與統治奠定了基礎,旗人享有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特權。
八旗對清兵入關和此後維持政局的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出征平叛,無役不與,因此被清朝統治者視為「國家根本所繫」。清廷在施政方面採取旗民分治的政策,在漢地的統治基本上沿用明制,而八旗卻在行政隸屬上則獨立於這一體系之外,保持在滿洲形成自身特有的傳統體系,因此又被稱為「國中之國」。八旗子弟「生則入檔,壯則當兵」,故以披甲從軍為主要職業,此外還可選擇出仕,他們在教育、科考、任職、律法等政治、經濟領域均享有一定特權,八旗成員從而控制國家的各個層面。
自清中後期,由於八旗人丁的滋生而兵額有限,閒散旗人增多,從而導致了八旗生計問題突顯。相對安逸的生活也造成了八旗兵丁逐漸疏於操練,給了湘軍等漢人地方武裝的崛起的機遇;另一方面,西方列強用新式武器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統治者嘗試對八旗進行改制以適應時局,但都收效甚微,無法阻止清朝和八旗走向衰敗。
民國初年,八旗衙門因《清室優待條件》獲得保留部分職能。1938年,隨着最後一支八旗組織新疆錫伯旗營被改編為縣治,八旗正式成為歷史。


創建之初
八旗制度的直接來源是「牛彔額真」(滿語:ᠨ᠋ᡳᡵᡠᡝᠵᡝᠨ,穆麟德轉寫:niru ejen),本為明代女真人出獵開圍之際臨時設立的「十人之總領」。1584年,出身建州左衛的努爾哈赤興起,牛錄額真,此後漢譯佐領,遂成為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且統轄規模擴大至300人[。努爾哈赤在征服女真各部的過程中不斷兼併部眾,佐領的數目也不斷增多,對主動來歸的部族,編隸時會考慮保持其血緣組織的完整性。努爾哈赤在每個牛錄設佐領1員,5佐領為1參領,設參領1員;5參領為1旗,設都統1員。都統之上為各旗旗主、領主,由努爾哈赤及其子侄擔任,為入八分王公。
1615年,建州已經吞併除葉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漢人也多有歸附。麾下牛錄已有百倍於起兵之初的規模。努爾哈赤在已建的黃白紅藍四旗的基礎上,再增設四旗,以原四色旗分別鑲邊。原有的四旗稱之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而稱新設四旗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從而形成了八旗之規模。
八旗集行政、軍事、社會、生產等職能於一身,對滿洲及清朝的崛起影響深遠。八旗作為行政組織,凡牛錄所轄之人皆為八旗社會階層中的部民,統治者以旗統之,發布政令。八旗將士「出則為兵,入則為民」,遇到戰爭時期由各旗從各牛錄抽調兵丁,作戰完畢後即回歸牛錄以耕養戰。八旗制度還把原先散居各處、互不統屬的部民整合在一個統一的組織當中,以旗-參領-佐領統治系統,建立起了一個井然有序的管理模式,使得來源不同旗人成為了一個不易分裂的整體。


清朝時期
1650年,多爾袞去世,順治帝開始親政。為了加強皇權,順治帝親自統領了原屬多爾袞的正白旗,由皇帝控制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稱「上三旗」,皇帝的戶口登記在鑲黃旗內,稱「鑲黃旗第一參領第一佐領上御名[註 3]」,故鑲黃旗為頭旗。由諸王公、貝勒掌控的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五旗則被稱作下五旗,其中正紅旗主為禮親王、鑲白旗主為肅親王、鑲紅旗主為克勤郡王、正藍旗主為豫親王、鑲藍旗主為鄭親王。
因八旗順序有別,所以旗人由於戰功或與皇室恩賜等原因從下五旗改隸上三旗者,稱之為「抬旗」;而在同一旗色或旗分之間的戶口轉換則稱之為「改旗」。
入關前,由於施行八旗領主分封制的緣故,各旗不論財物還是屬人對於入八分領主而言私屬性質都很強。但隨着順治帝規定天子親領上三旗,八分之制已徹底瓦解。為加強中央集權,清朝統治者開始剝奪旗主和入八分王公領主在各自旗內的權力。順治年間,開始以王公薪俸製取代旗主均分制,八旗議政之制也被取消。此後,王公對本旗軍隊的統領權也遭到了削弱。
雍正年間,雍正帝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他以儒家「天無二日」之論發布諭旨,將下五旗旗人官員與旗主王公、貝勒的從屬關係徹底廢除,僅保留各屬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權。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領,也由皇帝直轄。旗主對於本旗官員的任免權也被剝奪,八旗都統在康熙年間起施行跨旗擔任,以防旗主王公掣肘。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在北京正式設立八旗都統衙門,改變此前百餘年間,八旗都統「在府辦事」,無公所衙門的境況。
清朝前期,多數八旗子弟的生活水平高於普通漢人。然而,相對安逸的生活也造成了八旗兵丁逐漸疏於操練。清廷以「國語、騎射」為國策,然而至乾隆年間,京旗兵丁和各地八旗駐防均有疏於操練、武藝不精的現象存在。而八旗大臣中知兵者也越來越少。這些都給了清後期湘軍、淮軍等漢人地方武裝崛起的機遇;另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用新式武器叩開了中國的大門,統治者所倚重的「騎射」也被時代所淘汰,清廷曾嘗試對八旗進行改制以適應時局,及新式陸軍建立,將部分京旗部隊編為陸軍第一鎮,但均收效甚微,無法阻止當時內憂外患的清朝和八旗走向衰敗。1907年,清廷廢除旗民分治政策,然而僅僅4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


合符
「合符」通常指的是古代官員或使者所持的信物,用來證明身份或傳達命令。
圓明園八旗槍營,亦稱「圓明園內務府三旗護軍營」,是衛 戍圓明園及護衛皇帝的衛隊。合符用於調動軍隊,一般以金 屬打造,調兵者持陽符,軍隊持陰符,陰陽符相合則可調 兵。此一合符為製作正式金屬合符之前的木製樣本。
將領持有陽文合符,軍隊則持陰文合 符,兩者相合形成一種雙重確認機 制。合符除了作為調兵遣將的一種憑 證外,還象徵着皇權的威嚴與合法 性——只有持有合符的人才能發號 施令,確保了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和 權威。
清政府為維護封建統治、保障全國武器裝備的精良與製造供給,始終高度重視各類軍器的配置發放渠道及生產模式,並建立起獨特而完整的軍事裝備與兵工體系。這套體系對於清王朝的鞏固、繁榮與發展,以及在抵禦外來侵略、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團結方面,曾發揮過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根據清朝制度,無論是皇帝、宗室王公、八旗世爵、文武大臣,還是各省督撫總兵、八旗勁旅與綠營兵伍,皆身著甲胄,佩箭懸刀。各類軍器的形制、配給與數量,均按等級嚴明規定,從而形成上下鎧甲鮮明、四處刀光劍影的大清兵器展示場。 每人所配兵器的數量,如同頂戴、補服與俸銀、祿米一般,標誌著其地位、爵位及官階的高低。
實際上,特別是到了清朝中期以後,除了正規軍隊之外,宗室封爵者、總督巡撫等大臣已極少或完全不再實際操練兵器。數千卷的典章制度與訓諭詔令,大多被束之高閣,既無人過問,也未能有效執行。
皇帝御用兵器
甲冑分為大閱與隨侍兩類;弓箭則區分為大閱、大禮、吉禮、隨侍、行圍等種類,其中箭矢依照不同場合、活動與使用對象,更細分為數十種。以火槍為例:康熙帝擁有五種,乾隆帝多達十一種;盛裝弓箭的撒袋與佩刀則各備有三類。然而這僅是典制記載的部分,實際御用兵器數量遠超記載,且多數質地優良、工藝精湛、性能卓越,部分甚至可與當時世界最先進武器媲美——例如康乾時期多種「自來火槍」(即燧發槍)便屬此列。
宗室封爵兵器
親王、世子、郡王、長子、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等宗室王公,按制應配備盔甲、腰刀及撒袋,基本人手一副。至於弓箭配額則有明顯差距:弓具配置多者七張,少者兩張;箭矢數量依次為:3,000支、2,000支、1,700支、1,500支、1,000支、700支、600支、400支、300支、200支、170支。
世爵及文武百官皆配甲胄、撒袋、腰刀各一副,弓兩張。箭矢數量則依品秩高低等差配置,以五十支為單位遞減:公爵550支、侯爵500支、伯爵450支、子爵400支、男爵350支、輕車都尉250支、騎都尉200支、雲都尉150支。武官一至五品參照子爵至雲都尉標準,六品以下均為百支;文官配額略減。若世爵中官職高於爵位者,按官職標準配箭;爵位高於官職者,則依爵位標準配給。
八旗、各省官兵兵器
八旗分為京師與駐防兩大體系,內部又區分為滿洲、蒙古、漢軍三類。「其制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常備盔甲、腰刀配置與武職官員相近,主要差異在於箭支配額:從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驍騎校、領催至馬甲,配箭數量介於400支至50支之間。各省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各配箭400支;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及外委則依等級配置350支至70支不等。

刀劍天下
“北門外聚居著鐵匠,專門鑄造鐵甲;南門外則聚集製作弓與箭的匠人,專司打造弓矢。這段關於清朝開國戰爭時期手工作坊的記載,生動再現了當時兵器製作的景象。事實上,因清朝歷代皇帝對武備的重視,各類兵器的製作工藝均得以蓬勃發展。至清末道光與光緒年間,飛龍閣所藏御用兵器(不計箭矢)已多達數百件。現今故宮博物院與瀋陽故宮博物院擁有最豐富的刀劍藏品,其中最早的藏品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御用寶劍。然而有趣的是,這把太祖御劍實為明朝宮廷賜予其的「龍虎將軍劍」。
刀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兵器之一。據研究資料顯示,早在舊石器時代就已存在形制類似刀的打製石器。原始人用它來切割、砍劈、刮削,或處理獸皮。最初,刀是以生產工具的形式存在,隨後被賦予搏鬥砍殺的功能,其形制也逐漸定型。
自秦漢起,刀便區分為戰刀與佩刀:佩刀講究樣式別緻、鑲飾精美,側重裝飾效果及彰顯持有者身份;而戰刀因需用於生死搏殺,更注重實戰需求,要求刀體堅韌、重量適中,且整體結構設計須符合實用性。隨著生產技術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刀的分類方式日益多元。發展至清朝,御用兵器迎來鼎盛時期。由於歷代清帝崇尚武功,對御用兵器的製作極為重視,因而推動各類兵器的工藝發展。清代刀的種類尤為繁雜,包括腰刀、脾刀、背刀、窩刀、割刀、鴛鴦刀、船尾刀、繚風刀、滾背雙刀、雙手帶刀等,形式極其豐富多樣。
清朝初期處於連年征戰的歲月,製作材料匱乏、工匠稀少、工藝落後,即便是帝王御用兵器也難脫樸素風貌。例如清太宗皇太極的御用腰刀,無論是材質選用、製作工藝或裝飾技法,皆保留著清軍入關前原始簡樸的氣息。直至清朝中期,隨著帝國進入「盛世」,國力充沛、帝王追求風雅、工匠技藝日益精湛,此時製作的御用腰刀已逐漸失去實戰功能,轉而以華麗外觀為核心,製作愈發考究。除了傳統鑄造與鍛造工藝,更廣泛運用錾刻、鑲嵌、累絲、錯金銀等複雜技法。從乾隆朝製作的數百種御用腰刀與寶劍可見,其設計已臻化境,選材力求搜羅天下珍品,紋飾追求極致繁複華麗,即便今人觀之,仍不禁驚嘆其中蘊藏的巧奪天工之技與美學境界。
「天地人」款腰刀與寶劍
「天地人」款腰刀與寶劍向來聲名顯赫。據記載,清朝統治時期,紫禁城內的梵宗樓曾供奉乾隆皇帝御用刀劍,其中便包括廣為人知的高宗御製「天地人」款刀劍。然而清末動盪導致部分珍品流散宮外。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內務府造辦處接到皇帝旨意,歷時十年製作了寶劍30把、腰刀30把。因刀劍上有「乾隆年製」與「天」、「地」或「人」字號,故稱「天地人」刀劍。清宮造辦處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間,共打造四批御用刀劍,每批含腰刀30把、寶劍30把,總計240件。這些刀劍按「天、地、人」三款編號分級,每五件一組珍藏於48個楠木箱中:刀箱統稱「湛鍔韜精」,劍箱則題為「神鋒握勝」。
這過百把刀劍成為了清代宮廷武備的代表。這些有着不同樣式和名字的帝王專屬,必然也反映了製作的規律以及皇帝的個人意志。
異域進貢的刀劍
刀劍是向清廷進貢的代表性物件之一。精良的冰兵刃不緊彰顯華貴,盡獻武器亦有願為宗主國效力之意。
這三把刀分別見證了清朝三個重要歷史事件:乾隆45年班蟬額爾德及進京朝觐,以及準噶爾戰役與土爾扈特都東歸。
「水斷蛟龍薄析兕,光連星斗氣如虹。」此乃乾隆皇帝在御製《題廓爾喀貢刀六韻》中對廓爾喀 (現今尼泊爾一帶)進貢寶刀的評語。雍正時期,清廷與廓爾喀曾維持封貢關係,其後中斷。軍事征服後,戰敗一方往往通過盡獻武器來表求和意。 至乾隆五十八年,歷經兩次戰役後,平定廓爾喀進犯之後,廓爾喀向清廷稱臣,成為清朝藩屬,雙方重建友好往來的封貢體系。廓爾喀素以鑄刀技藝聞名於世。廓爾喀於乾隆57年開始進貢兵刃。其兵刃既保留地域特色,又深受莫臥兒帝國兵器形製與裝飾工藝的影響,衛青工刀劍收藏增添了異域風情。
「天朝上國之榮光,從萬國來朝之盛況便可見一斑!」在古代,衡量國家強盛的標準,往往體現在藩屬國的數量多寡,以及該國國民在異域所受的禮遇程度。
作為清朝重要的藩屬國,琉球多次向清廷進貢刀劍。除藩屬進貢外,清宮還通過外交往來、市節互換及商業貿易等多元管道,廣納域外兵器。這些來自不同地域的刀劍,寄豐富了皇家收藏,又展現了清廷"富有天下"的氣象與格局。





騎射與槍炮
清朝的騎射是滿族的看家絕技,是建立和維護清朝統治的關鍵;其內容包括騎馬和射箭,自努爾哈赤時期萌芽,並在八旗制度下確立並貫徹,特別在康熙、乾隆時期達到頂峰,透過嚴格的官學教育、武舉考試和木蘭秋狝等實戰訓練,將其制度化,是清朝維持其軍事和民族傳統的基礎,儘管後來隨著火器普及和八旗腐化而衰微,但仍是清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眾多兵器之中,弓箭佔有顯著地位。清廷將弓矢騎射列為祖制,並載入國家法典,告誡後世永遵勿替。順治皇帝曾明確指出:「我朝勘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將單一兵器的地位與作用提升至如此高度,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 正因如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皆對弓箭格外青睞與重視。雍正皇帝更斷言:「自古以來,各種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斷未之有也。」應當承認,後金及清初時期的弓箭確實為新政權的建立與鞏固立下顯赫功勳。在傳統兵器體系中,當時的弓箭無論在射速、靈活性,還是殺傷威力方面,確實具有其他兵器難以比擬的優勢,因而始終受到官方重視,長期作為戰場上的主要武器。
清朝鼎盛時期的幾位皇帝都重視騎射,其中最身體力行者當數乾隆帝。《乾隆禦制詩五集》卷廿五中有《騎詩》一詩,在注中提到他十二歲即陪康熙帝“臨門騎射,每因射中,荷蒙天語褒嘉”。乾隆帝每年要舉行圍獵騎射,親自倡導,在他八十歲時還親臨木蘭打圍。據《清朝野史大觀》,每年夏季接見完武官之後,乾隆帝即率百官至宮門外“較射”,如官員較射三箭不中,立刻予以斥責;秋歲出塞時他也要較射,每次都是三矢三中。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他於南苑大西門外連射九矢,竟無虛發,可見射術之高。乾隆帝認為:“本朝以弧矢得天下,豈可忘本?”為了保持武士的“尚武”傳統,他不僅身體力行,還制定了各種規章,特別強調八旗子弟自幼就要學習騎射。
旗人家的男孩降生後,要在大門上懸挂弓箭,預示將來有弓馬前程。弓箭是旗人家幼童的玩具,以柳木為弓、荊蒿為矢、鳥類為羽,幼童攜自製小箭,每人出兩枝豎立一堆,距三十步遠,依次射中得箭,“孤矢之利,童而習之”。正因為自幼練習,旗人十幾歲時,便已善於騎射了。
清朝板指
清朝板指最初是滿族射手用來保護拇指的實用工具,後來在乾隆帝的推廣下,演變為象徵身分與地位的裝飾品,材質也從鹿角等獸角豐富至玉、象牙、金銀、珐瑯等,並發展出素面「武扳指」和雕飾精美的「文扳指」等樣式。
-
實用工具的起源 - 板指的前身是「韘」,是一種在射箭時套在拇指上勾弦的器物,可保護手指免受弓弦的傷害。
-
滿族傳統的象徵 - 乾隆帝極力推崇滿族的騎射文化,將板指視為尚武傳統的象徵。
-
身份與地位的象徵 - 在清代中晚期,佩戴板指盛行,尤其在旗人之間,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
-
材質 - 清代的材質變得豐富多樣,包括玉、翡翠、瑪瑙、象牙、金銀、珐瑯等。
-
文扳指:: 外壁刻有詩句花紋,用於觀賞和把玩。
-
武扳指:: 素面,主要用於實用功能。
騎射飾物
清朝皇帝擁有良馬達二十萬匹,由上駟院管理,主要牧場在北京南苑、內蒙商都達布遜諾爾、盛京(今瀋陽) 大凌河和外蒙的達里岡愛牧場。他們喜愛馳騁馬上,不論是驅策戰馬的馬鞭,或是用於召喚獵物的鹿哨,都精美異常。在騎射遊獵之間,形成獨特的尚武美學。
槍炮
清代火器以火炮與火槍為主體。統治者透過對明軍作戰及清初平定叛亂的經驗,深刻認識到「欲攻敵非炮不克」的戰略需求。康熙三十年(1691年)特設火器營,配備槍炮分發八旗,自此「我朝之神威蓋震於四域」。火器營分內外二營,內營炮營配置火炮四十位,標誌著清軍首支獨立炮兵與火槍部隊的誕生。清廷在火器種類、性能與數量上持續創新發展,使武器裝備體系顯著提升。
京師武備體系中,火炮配置充實且種類完備。乾隆年間漢軍八旗約配備銅鐵火炮六百位,至嘉慶朝各旗配置數為:鑲黃旗六十九位、正黃旗七十九位、正白旗六十九位、正紅旗七十四位、鑲白旗六十二位、鑲紅旗六十八位、正藍旗六十五位、鑲藍旗七十二位。北京內城九門、外城七門均築有防禦性甕城,共部署「神樞」「得勝」「法功」「紅衣」「神武」等各型火炮達一千九百三十七位,隨時可補充各營作戰需求。
八旗軍入關後陸續組建專屬炮兵部隊,其中子母炮成為其特色裝備。清代子母炮係由明代佛朗機炮演進而來,標準配置為一門母炮搭配五發子炮(呈長體炮彈形制)。作戰時將子炮自母炮後膛裝填,首發射擊後可迅速更換子炮,省去傳統火炮需重新裝藥、搗實、填彈等繁瑣流程,大幅提升射擊效率,堪稱早期速射炮,形成顯著火力優勢。
雍正皇帝總結歷代戰役經驗,明確指出「子母炮軍中最緊要利器」,遂於雍正五年(1727年)頒旨八旗,在原有每旗配備6門的基礎上增設4門,確立每旗標準配備10門子母炮的定制。此項革新不僅強化清軍火力結構,更展現清代對火器技術的戰略性運用與制度化管理。


測炮象限儀
測炮象限儀是清朝乾隆年間由清宮造辦處製造的火炮測量儀器,現為故宮博物院藏品並收錄於《皇朝禮器圖式》。其主要功能是測定火炮發射時的仰角或方位角,並配合角度計算目標距離。使用時置於火炮之上,透過游標小孔觀察目標以完成測量。這件器物不僅具備軍事技術價值,也承載了清代軍事與禮制文化的歷史意義。

操閱與軍禮
操閱
中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浩浩湯湯的軍事史貫穿了整個社會發展的進程。閱兵作為傳統軍事儀式,以田獵為最初方式發展演變至今。《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指國家的公祭儀式,「戎」是國家的軍事行動或戰爭。閱兵儀式,既是「祀」,也是「戎」,是當之無愧的國家大事。
清代的簡閱又稱校閱,是八旗、綠營由王、大臣或督撫定期檢驗部隊教練的制度,也是促進軍事訓練的手段和形式。大閱是皇帝檢驗部隊訓練成果,考察部隊戰鬥力的隆重閱兵儀式。早在天聰年間,皇太極就曾舉行過大閱。此後,乾隆、嘉慶等皇帝閱兵的記載不斷出現在各類文獻中。雍正以後,大閱制度更加完善、周密。乾隆三年(1738)規定,以後大閱,皆按照順治十六年定例三年一次,其辦理事宜照雍正六年規定舉行。清代大閱的地點,主要在南苑、盧溝橋、玉泉山、多倫諾爾(今內蒙古多倫)、暢春園等地。
八旗閱陣圖
除皇帝親自閱兵外,清代還形成了多種閱兵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欽派檢閱,由練兵處、兵部、陸軍部奏請皇帝,欽派知兵大臣數員前往閱兵。閱兵內容有「軍容、軍技、軍學、軍器、軍陣、軍律、軍壘各項」。乾隆帝還針對一些大臣只在帳幕內互相對閱,並不親赴隊伍操演的情況,規定「八旗合操時,閱兵王、大臣等,逐次前往監看稽察,如有無故不到者,同閱之王、大臣指名題參議處。」宣統三年(1911)七月二十四日,監國攝政王載灃就於德勝門外的鑲黃旗、正黃旗兩旗校場檢閱了皇家禁衛軍。
陸軍會操圖
校閱陸軍報告
健銳營操演陣圖
健銳營原是專業攻城部隊,乾隆十七年後,陸續擴充其他專業部隊,乾隆三十年時,擴充至三千人,被乾隆讚譽為「所向無敵,實為得力」,也常被派遣出征,是清軍的精銳。
健銳營操演陣圖餵介紹該部操演的圖冊,內容包括了四種陣法、一種馬上技術和三種步下技藝,展示這支精銳部隊操演的內容。
健銳營作為特種部隊駐扎香山后,平時在各自營房訓練,定期到演武廳進行合練,並接受皇帝的檢閱。有史料記載,自團城演武廳興建后,乾隆、嘉慶、道光等多次到此閱兵。尤其是作為健銳營的創建人的乾隆皇帝,每次閱兵之后還即興賦詩,鼓勵八旗將士。僅《日下舊聞考》就記載了御制閱武詩15首。
據傳,有一年秋季,乾隆皇帝在演武廳檢閱完八旗將士后,即興換上一身戎裝,騎上駿馬,手勒馬?,腰挎劍囊,隨即策馬揚鞭,馳騁於演武場上。眾將士一見,山呼萬歲,隨即也策馬揚鞭,尾隨其后,演武場上塵土飛揚,殺聲一片,場面好不壯觀。清代畫師曾繪制《健銳營演武圖》,形象地描繪了乾隆時期健銳營士兵進行合練,接受檢閱的情景。
軍禮
軍禮作為西周五禮之一,起源於西周,主要用於軍事活動相關的禮節儀式。古代軍禮涵蓋出征祭祀、凱旋效勞等禮儀,按四季分為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其形式包括拱手禮(如周亞夫見漢文帝)和跪拜禮。鴉片戰爭後,西方軍禮(如舉手禮、注目禮)隨晚清軍事近代化傳入中國。
西周起源:軍禮作為「五禮」之一,初為征伐之禮,後擴展至軍事操演、田獵等。
禮制發展: 周代設有大師之禮、大均之禮、大田之禮、大役之禮、大封之禮五種形式。 出征前舉行祭福儀式,以三牲鮮血祭祀天地。
晚清轉型: 甲午戰爭後,清廷推行《陸軍行營禮節》,採用西式軍禮。 《陸軍行營禮節》(軍禮)的核心在於表達尊重,主要包括舉手禮(最常用,戴帽或不戴帽皆可,右手五指併攏向帽簷或太陽穴)和注目禮(在不便時使用),以及特殊情況下的舉槍禮/扶槍禮(現今主要用於閱兵儀仗或特定場合,如持槍時以右手或左手扶槍或舉槍示意)。禮節動作要求軍姿挺拔,眼神專注,體現軍人素養,不同場合和武器有不同規範。

防禦國彊
清代防禦國疆的策略是「重陸輕海」,主要體現在對陸疆的經營(如新疆、蒙古)與對海疆的相對忽視,清初透過康雍乾盛世鞏固了廣袤疆域,但後期海防鬆懈,直到晚清甲午戰後才意識到海防重要,雖有洋務運動改革,但因積弊已深、思想落後(如「海防塞防之爭」中的塞防派主導),最終未能有效抵禦西方列強與日本的侵略。
康熙中期,東南沿海叛亂平定後,清廷建立起砲台和帆船艦隊構成海防體系。 嘉慶年間,海盜曾猖獗一時,但海上秩序上能夠得到控制。唯十九世紀中葉後,西方海軍強權崛起,中國傳統海防體系已難以應對。自鴉片戰爭起,連場對外戰爭,均以戰敗收場,清廷遂進行變革。 同冶初年,清廷在福州設置船政局,培養人才,並建造輪船,積極營建西式砲台。
光緒初,清廷成立總理海軍軍事務衙門統籌全國海防,由酸親王奕環和李鴻章等負責,籌備了史上第一次王大臣海軍校閱。然而這些軍事變革未見成效,在與列強的軍事比拼中仍處於下風。數年之後,北洋艦隊覆師於黃海,终在與列強的軍事應對中,走向王朝統治的結束。防禦海疆的重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始能實現。
陸防與疆域經營
-
新疆(準噶爾、回部):清廷投入大量資源平定準噶爾叛亂,設立新疆都統,推行改土歸流,將新疆有效納入版圖,形成穩固的西北防線。
-
蒙古(漠南、漠北):早期採取羈縻政策,後期推行改土歸流,重點在於防止蒙古部族與內地衝突,並防範俄國勢力滲透。
-
長城:仍為重要防線,但清代主要用於內部控制(如八旗與漢人),而非單純的對外防禦。
-
西南(雲南、西藏):平定大小金川及西南土司叛亂,確立了對西藏和西南邊疆的有效控制。
海防的薄弱
-
傳統陸權思維:清朝本質上是陸權國家,早期統治者更關注內陸與北方邊患。
-
明末海防遺產:明末的海防力量在清初消耗殆盡,加上禁海政策與內亂,海防幾乎癱瘓。
-
後期改革的局限:洋務運動雖建立近代海軍,但甲午戰敗後轉為保守,多購淺水炮艇,未能真正形成強大海上防禦。
清代在前期成功開拓並鞏固了廣闊的陸疆,但因“重陸輕海”的戰略思想,導致海防建設滯後,錯失了應對西方海上挑戰的良機,最終在晚清的國防困局中,陸防與海防都未能有效抵禦外敵入侵,國疆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渤海閱師圖
光緒十二年四月,醇親王奉慈禧太後懿旨巡閱北洋水陸各軍,從天津出海,前往旅順、威海、煙台等地視察海旁設施與海軍艦隊,是清皇朝最高規格的海上軍事校閱。過程中他赋詩為記,並命攝影師梁時泰和來歆克參與攝影。《渤海閱師圖》是記錄這次校閱最重要的官方繪畫,結合了西方照相術、工程圖和輿圖的技法,呈現出此至海軍教育的精彩歷程。
10幅彩色冊頁描繪醇親王奕讚(1840-1891年)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巡閱北洋海防的重要時刻,出自隨行的神機營畫家慶寬(1848-1927年)等人。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王公大臣校閱海軍,然而清廷此後多以攝影方式記錄巡閱,此作品堪稱傳統宮廷軍事繪畫的空前絕後之作。
滿族重視先祖尚武精神,提升製造弓箭、刀劍和槍炮等武器的技術,勤於圍獵和操演,創造大量宮廷軍事藝術作品和創建軍事禮儀,發展艦隊和海防等措施。清朝統治者透過戰爭奪取天下,維持強盛的戰鬥力對維持政權十分重要,即使是和平的年代,清廷亦會打獵、操演等以保持軍事實力。
《渤海閱師圖》之〈廟島蜃市〉
光緒十二年(1886年)四月,醇親王奉慈禧太后(1835–1908年)懿旨巡閱北洋水陸各軍,是清王朝最高規格的海上軍事校閱。十八日下午二時,醇親王從旅順出發,前往威海衛,船行四十餘里至廟島時,看見海市蜃樓奇觀,命令隨員慶寬(1848–1927年)等照繪,〈廟島蜃市〉即為此圖。根據隨行官員周馥(1837–1921年)所編《醇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此次難得一見的海市蜃樓景象據描述為「樓台隱見,林樹扶疏,樹外若有數僧翹首立迎」。

清代戰圖
清代戰圖是乾隆時期為彰顯「十全武功」而由宮廷畫師繪製的紀實性軍事繪畫,融合中國傳統繪畫與歐洲銅版技術,以細膩筆觸展現平定大小和卓之亂、林爽文事件等重要戰役。其題材旨在歌頌君主功績,代表作品如《平定臺灣戰圖》、《平定西域戰圖》,不僅記錄清朝對外征戰的勝利,也體現中西藝術交流成果。製作上由宮廷畫師繪製底稿,再送往法國雕刻師以銅版技術精細雕刻印刷,成品風格精緻。這些戰圖既是宮廷軍事藝術的重要代表,也是研究清代軍事史、藝術史與文化交流的珍貴史料,部分原版銅版現藏於海外博物館,見證了清代武備與疆域的強盛。
《平定雲南貴州戰圖》是清朝為記錄平定雲貴地區反抗起義而繪製的12幅系列戰圖,由醇親王總監、慶寬等人繪製,描繪了清軍如何攻克府城、土城等關鍵戰役的場面,展現了當時的軍事策略與功勳,是珍貴的清代宮廷繪畫與軍事史料。
此畫卷記錄同治年間雲南、貴州地區回民起義的軍事行動,共十二幅,呈現攻城戰事的重要節點,並詳實描繪山川地勢、攻城器械、部隊部署與戰鬥細節。畫卷兩側附有皇帝諭旨,述說戰役經過、嘉獎將領功勞,以彰顯武功。其繪製目的在於褒獎軍功、鼓勵將士,並將清朝的軍事成就與勝利過程永久留存。此作結合繪畫藝術與軍事史,具備重要的歷史與研究價值,是探討清代軍事與宮廷文化的珍貴資料。
乾隆年間製作的各類銅版畫戰圖中,《平定回疆圖》(又名《平定伊犁回部得勝圖》)是當時製作時間最早者。全圖自起稿到雕刻,皆委由西洋畫工參與,是具體呈現中西文化藝術融合的傑作。
《平定回疆圖》所描繪者,係清高宗於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三年(1758)和二十四年(1759)平定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首領達瓦齊、阿睦爾撒納,以及回部大小和卓木布拉泥敦、霍集占挑起叛亂的主要過程。據《活計檔》所載,隨著乾隆二十五年(1760)西陲戰況大致底定,高宗命令宮廷西洋畫師郎世寧、艾啟蒙、王致誠、安德義四人著手以絹草繪圖稿。
乾隆二十九年(1764)命郎世寧等人將原先的圖稿畫大,其正式稿樣陸續發往廣東粵海關,運往歐洲法國承辦。圖樣運抵法國後,法王路易十六相當重視,特委由法國皇家藝術院挑選良工製作銅版,務求精細。從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三十九年(1774),歷時六年,製作完成。透過法國東印度公司前後運返中國,計含金屬銅版十六塊,銅版畫二百套。本件為格登山斫營圖,縱五六公分,橫八九.五公分。本圖描繪阿玉錫率騎兵夜襲準噶爾部首領達瓦齊在格登山的營區,準噶爾部潰不成軍清軍大勝之場景。畫面生動逼真,刻畫細緻,極富立體感。
《靖海氛記》原是順德袁永綸的著作,清道光十年 (1830年) 11月於廣州出版。書中記述兩廣總督百齡瓦解十八世紀晚期以來肆虐廣東沿岸的海盜禍患。此卷軸描述的情景與《靖海氛記》一脈梳承,故命名為《靖海全圖》。
鄭一於清嘉慶年間(1802至1807年) 統一各海盜幫眾,其妻鄭一嫂(石香姑) 和張保繼承其後,進一步擴充實力,擁有船隊6支、部卒7萬、船艦2,000嫂、火炮5,000 – 6,000門。其船隊操控廣東貿易的3條海路,袁永綸亦對二人作出論述。
《靖海全圖》描述百齡剛柔並施,既剿捕、又招安,得以掃平海盜。而此畫卷其中一個引人入勝之處,就是百齡在畫卷共出現9次。